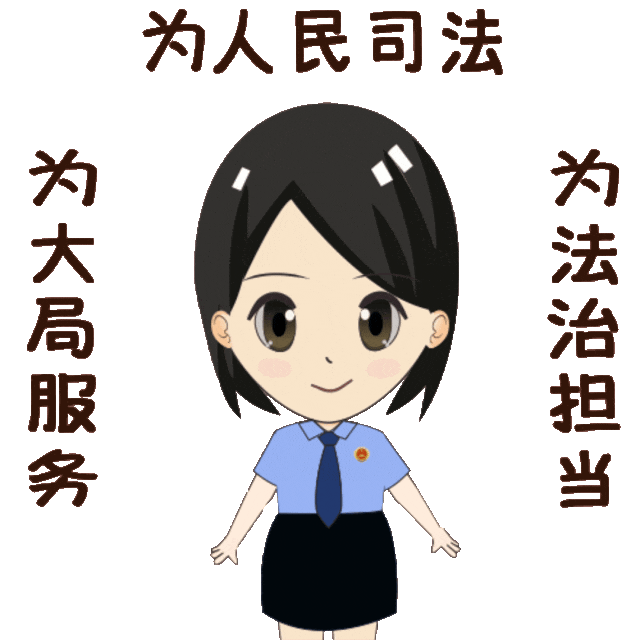我时常想,是谁在《诗经》开篇写下了第一个文字,如果人类当初不将自己生命中的敏感与忧伤交付诗歌,那么今天,我们的生命会怎样?一直对那句熟悉的鼓词耿耿于怀,“诗书误我,我误春光。”它像一朵充满悲情的红罂粟花,时常在我生命的潜意识里盛开。可是,生命中没有如果,而诗歌也不代表忧伤。不是吗?
我时常想,也许性格使然,也许宿命作怪,一颗敏感的心总会莫名其妙地在一瞬间沉落下去,悲怆扑面而来,唯美由心而生。沉重的心,软弱无力,总使你无法逃遁锦绣文字的疼痛利刃。也许,文字的初始只是中性符号并无善恶性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只是移情外物的表达方式。因此在华美的篇章里,一种大悲悯总缠绕着千古文人那细细的脚踝。无病呻吟吗?非,真性情也。
我时常想,人类生命,本是不断失去与找寻的过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在寻找什么,只是那一种失去与寻找的感觉,让我们永锡难忘。在这活与痛的冲突中,在爱与生的烦恼边缘里,与自己失之交臂的找寻心理总喜欢用疼痛的文字来呈现。但每每是无声胜有声,我们钟情的文字也有空白的无力,表达的无助。生命疼痛文字的啊,属于永远的后知后觉,印证了那一份永远的无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应当是混沌人类使用文明记号——文字永远的悲哀吧!
尽管每天我的笔都在孤独和奋进的漩涡中冲突奔流,但却时时能感到那逝去的幸福汪洋!尽管每时都有对往昔那撕裂之美的深深回忆,但坚毅性情的脸庞却从不落一滴泪。
也许在银色的沙滩上,生命的痛苦只是藏在那五彩贝壳里的一粒沙。一天天吞咽着海蚌的泪!沧海桑田,万古洪荒后,也许它的魂灵会成为那一枚镶嵌珍珠的琥珀。深深藏在沙堆里,静静躺在那里,听着海浪和海鸥的声音。
也许千年之后一个明媚的夏日,就在这片蓝天白云下,就在这片沙田上,黛黑色的海鸟群里有一只湛白色的鸟,不知它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只知道它的翅膀上写着有我文字的诗歌,它孤独的影子在蹁跹、低飞、徘徊,猩红色的喙衔着一粒石子,飞向大海的深处,万古洪荒后这粒石子在金色的沙滩上发了芽。
我知道人类高贵的心灵若是一眼清泉,那么文字疼痛的思想就是西天的一抹晚霞。在夕阳的余晖里,我愿我的诗篇做一只白鸟,天空中虽没留下什么痕迹,但我已飞过!
我知道生命的痕迹只是一尾游泳的鱼,那鱼的心脏和眼睛便是那块幻化为我的千古琥珀和珍珠。在呼吸的每一刹那间,我都能感到那跳动的沧桑之美!
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另一棵青草,一朵浪花拍打另一朵浪花,一阵轻风追逐另一阵轻风,我相信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