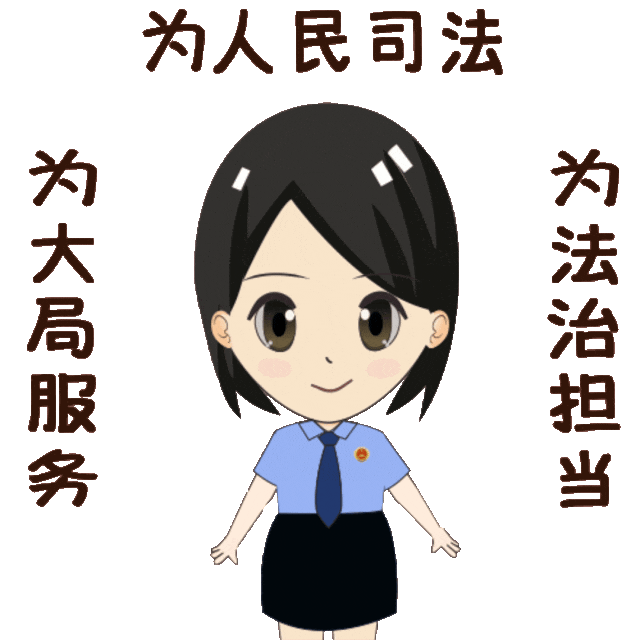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父亲早逝,他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外祖父家可谓书香之家。他在《文字生涯》一书中写道:“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一年只在十月开学的时候打扫一次,平时不许掸灰尘。”他的外祖父很有文化,然而这并不耽误他的外祖母成为通俗小说追逐者。萨特对外祖母的阅读,有一段惟妙惟肖的描述:
“在外祖母房间里,书是躺着的,这是她从一家阅览室借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超过两本。这种无价值的装饰品使我想起过年吃的糖果,因为书页柔软而发亮,很像裁剪好的铜版纸。纸张光亮、雪白,几乎是新的,总带着点儿神秘感。每星期五外祖母梳妆打扮一番,出门时对我们说:‘我还书去。’回家后,她摘下帽子,卸了妆,从手笼里取出书来。我感到蹊跷,心想:莫非还是那两本?
“她精心地包上书皮,不让人看封面,然后选择其中一本,在靠窗口的安乐椅里坐定,戴上圆框眼镜,疲乏而安乐地叹口气,垂下眼皮,脸上浮现出一种美滋滋的、机灵的微笑,这种微笑我后来在若孔德夫人的嘴唇上重新见到。母亲默不作声,也请我不要说话。于是乎,我想到了弥撒、死亡、睡觉,我浸沉在神圣的静穆中。
“不过,我不喜欢这种装订的书,太讲究了,这是我们家的不速之客,外祖父老是不客气地说这些书只为不懂事的人所崇拜,只有娘儿们才欣赏。星期天,他闲着无聊,走进妻子的房间,直挺挺地站在她面前,但无话可讲。众人望着他,他劈里啪啦地敲打玻璃窗,实在想不出新花样,便转身走向路易丝,突然从她手中抢走小说。她怒冲冲地叫道:‘夏尔,你干什么?我念到哪儿了?一会儿该找不着啦!’但见他趾高气扬地朗读起来,突然用食指敲敲书,说道:‘不懂!’外祖母说:‘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从当中念起的呀!’于是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扔,耸耸肩走了。”
很显然的是,萨特的外祖母读的是通俗小说,他还补充道“外祖父绝对不会错的,因为他是内行”……看了所谓的“通俗”,常常是“低俗”的代名词,为人所不屑。但有人就是喜欢,你也管不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其实也很烂,真正好看的也就那么少数。请注意,我这里说的还仅仅是好看,还不是好。我业余喜欢看外国通俗小说,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好,因为好看的实在太少了。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真正的垃圾,包括许多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比如有位JamesPatterson,号称头号畅销作家,这位先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可见,即便是身为行家,有时也忍不住要去读垃圾文字。
美国著名影评人保利娜·凯尔有一段关于人们为何会看烂电影的描述,写的特别风趣。“电影里那些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在发现这个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烂得多以前,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和他们一样,几乎所有人都四处漂泊,背井离乡。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可以躲进电影院,银幕上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倍感亲切——过去的理想和我们一起变老,看上去也不太理想了。在哪里能像在一间俗丽而又乌烟瘴气的电影院里看一部烂电影更能激起我们的受虐欲?电影和无名之辈是绝配。电影——这个庸俗堕落的世界所特有的庸俗堕落的艺术,和我们的感觉很搭调。世界已经不是教科书里所讲的样子,而我们也辜负了父母和老师的期望。电影是一种廉价而又容易的表达方式——唯我们所有;它是无家可归者的烦闷阴沉的艺术。因为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就在懈怠中堕落,在不负责任中放松,当看到一个枪手用一颗子弹打死三个排成一排的人我们也许会咯咯笑上一分钟,这种场面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如幼儿园老师讲的《勇敢的小裁缝》真实呢。”
这一段话,也许说到了很多观影人心里去了;要不然,怎么有些烂片片场的人数也是乌泱乌泱的呢?
诚然,就观影而言,不少人喜欢或习惯于堕落,相对于往上走,堕落更容易一些。这跟读书一样,人们宁可读网络小说,也不愿意去碰经典名著。正如昆德拉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言:“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发晕是怎么回事?是害怕摔下去?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我们怎么还发晕呢?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木心说:“人生恰如监狱中窳劣伙食,心中骂,嘴里嚼。”监狱里的伙食是没的选择的,而自由人明明有选择空间,却最终倒向劣质的烂东西。很多人明知道垃圾食品缺乏营养且对身体有害,但还是大口嚼着垃圾食品,有时只是因为便利,懒得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