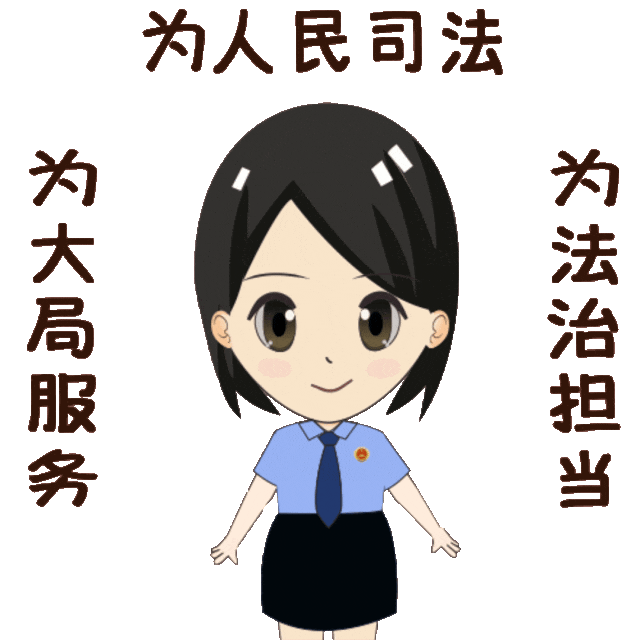屋里只剩下我跟那个嫌疑人。我把钱给了内勤,打发他到饭店买馅饼。
办公桌对面有把椅子,是我给嫌疑人搬的。可他说圪蹴惯了,便靠墙蹲下。他的头上戴着个旧黄帽,帽顶上有个洞,一撮花白头发从洞口探出。他那双枯瘦的脏手,十指弓曲着捂在满是皱纹的脸上。这脸让我想起耕过的土地。他的下巴抵住前胸,不时地狠狠吸一口气,然后就“唉——”地呼叹出来。
“兄弟,”他把手从脸上松开,“是不是真的就不叫我回家啦?”他那土灰色的眼珠凝视着我。
我点点头。
“兄弟呀兄弟,可做不得呀兄弟!”他连声急急地说,说完,那惊恐悲戚的老脸又一下子显出笑意。“兄弟你哄我呢……你……你看,我就知道兄弟你哄我呢。”他说。望着他那可怜巴巴又带着乞求和期盼的神色,我摇摇头。他“唉”一声,又将原先也没离开脸有多大距离的十指,重新捂在脸上。屋里极静,远远地传进外面街市上热闹又嘈杂的声音。“多会儿才叫我回村?”他又抬起头把脸露出来,问。我又摇摇头,没回答。
他是内蒙古农村的,前些时搭顺脚车来大同卖葵花子,有几个小孩问他要不要废铜,他说要。先后共收了四次,最后一回在废品收购站出卖时,被我们给逮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被孩子们烧得焦黑烂污的铜丝,原来的价值竟有5000元。工厂库房的损失由孩子们家长赔偿,他,我们决定法办。根据案情,估计最少也得判他两年,要知道他当时赶上了“严打”。我看着他那愁苦的样子,没忍心说实话。
“三五个月内,都甭想回去了。”我说。
“啥?!”他惊叫一声,想要站起来。大概是由于蹲得过久,反倒一屁股跌坐在墙根,破帽子掉到地下也没去拾。“兄弟兄弟行行好吧,这可是要我老汉的命呢!”他一下跪起,向前膝行了几步又趴在地上,冲着我连连地磕头。
我先是一愣,后来赶忙过去一把将他揪起,又把他按在椅子上。我又弯腰捡起破黄帽,在桌腿上拍打两下后,搁在他的头顶。
“这可是天塌下了这可咋办呀!”他痴痴地盯着地板,自言自语,“女子,儿子,这下他们可咋过呀!”我猛地想起做笔录时,知道他家只有一个19岁的闺女和一个6岁的儿子。“村里没有亲戚?”我问。“亲近些的就一个姑姑,可太远。好几百里。”我也不由替他犯了愁。“兄弟,能放我回村安顿安顿行不?安顿好就来行不?”
这怎么可以呢?
“这样吧,”我想想说,“有什么好安顿的,你跟我说,我写信转告他们。或者我亲自去一趟也行。”他看我。“信不过?”我问。“信过。信过。”我准备好纸笔。他却隔了老半天才张嘴:“你告诉孩子们,就说他爹在外头做了灰事了。不不不。这样说是不可以的。”
他停下来想想又说:“不知道你给不给这样写,就说你们的爹在外头找到营生了,得过个半年六个月才回去。你……你再告诉给孩子们就说,米瓮里头往深探探有一百块钱。明年那责任田该种莜麦,还让八叔给种,等爹回去再结算工钱。再,再……再告给小子就甭念书了,跟姐姐在家里做营生,等爹挣了大钱再,再念……还得告给女子甭理那谁,那是个坏人。黑夜里万万千要记住把狗拴住,好,好壮个胆子……再就是,要是有个灾有个病……病,病啥的……”
他语言结巴,说不下去了。我没催他,静静地等。我也没抬头看,我怕他看见我眼眶里有泪花在滚动。
他拿帽子擤了几声鼻子,隔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告给孩子们要好好儿躲对,万万千甭有了病……万一有个啥,泥瓮里有黑糖,化上水是下火的……”
我的鼻子发酸,实在是不能再听下去了。我将笔搁在桌子上。
他把手伸进后腰里,摸出一个东西,颤颤巍巍地放在我的玻璃板上,说:“这个看能不能装信里。唉,女子要了好几回,这次才,才给买……”透过模糊的泪,我看见的是个蓝色的“维尔肤”小油盒儿。“你再告给……”
“别说了!!”我“啪!”地一拍桌子,冲他大吼。他一惊,帽子又掉到地下,红肿的眼瞥了一下我,又赶快看别处。
“怎么回事儿?”内勤进来了。端着个洇出油渍的报纸包。“没,没什么。”我把脸扭向窗外。
“吃哇。这是惯例。我们的组长请客。”内勤哗哗地把纸包展开,说。
“不,不不。我咽不进去。”
“吃!!”我猛地转过身喝令他。我想在喝吼声里将胸中憋得难受的气一块儿喷出。
“吃,吃。我吃。”
他把馅饼大口大口填进嘴,填得两腮鼓鼓的,同时,眼里扑棱棱地滚下两行泪蛋。